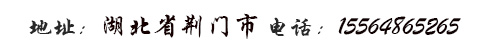故乡冬天里有没有童话
|
文/曹鼎毅 我的故乡叫西阳庵,这名字在庄河市地理标记上你也找寻不到。原因是当初户口普查登记时,不知是登记员出差还是派出所户籍管理登记有误,反正现在的身份证上都写成“西阳俺”。一字之差,不伦不类,没了“广”字头,加个“人”字旁。现实的情形是,庵被拆了,成一片废墟;人渐渐稀少,只六七十人,竟成反谶。随着乡人寻根文化意识的觉醒,会追根溯源,改回“西阳庵”。相信那时自己一定是摇旗呐喊者。 叫西阳庵,有讲究,是因为这里曾有一座姑子庙,女性修行者居住的寺庙,就叫庵,也有写作“菴”的,异体字而已。中国的寺庙建筑,至明清时逐渐形成两种建筑风格。一种是官建的大寺,规模宏大,风格华丽,且大多建在城市或其附近,所谓大家闺秀;另一种是山林佛刹,多建在名山胜景风物佳丽之地,清新雅致,纯朴淡素,所谓小家碧玉。姑子庙当然属于后一种,一来风水肯定是不差,二来远离尘世的熙攘,利于修身养性。为啥叫“西阳”,不可考,但还有叫“东阳庵”的,许是佛教的一种布局。在重建庙宇道观为灵魂救赎的当下,家乡真的有热衷者想原址重启,确有规划方案。以庵名为屯名,理所应当。这是让故乡人颇感自豪的历史归属感和风水文化荣耀感。一只飘飞空中的风筝,回头看看,总有一丝绳线告诉它,根在哪里。 小时候听到的一些故事可为这里风水佐证。一户垦荒者,家里的牲畜丢了,找了三四里地,发现有庵庙在此,住了好几年,竟不知道。一名尹姓先人,在山上和豹子遭遇,殊死一搏,侥幸脱身,让后人颇以此为豪,以致数辈下来,族中人仍多熊腰虎背者,家传如此。母亲小时候,给躲在山上的四姥爷送饭。那时国民党抓壮丁当兵。四姥爷就在桲椤树杈上搭建个栖身地,保长愣是找不到。母亲把吃的用的装在粪筐底部,上面覆盖些牛羊粪,躲过盘查,一路送去。我小时候,还有鸻鹘,只要飞临村庄上空,大人小孩就敲着锅瓦瓢盆,否则就会有鸡鸭或者羊羔被鸻鹘抓走。 那时的故乡相信一定会有童话的,只不过孩子们不知道啥叫童话,生灵们也不知道啥叫童话。谁做童话里的公主呢?爱谁谁吧,孩子和小动物们你方唱罢我登场…… 我是年出生的,姑子庙给我的印记很朦胧,只记得有花花绿绿的色彩,让我很害怕的大眼珠子和随时会砍下来的长剑阔斧。到七岁八岁讨狗嫌时,就看到有一帮胳膊上箍着“红卫兵”袖标的大哥哥们把佛的眼珠抠出来当溜溜球玩,庙里的戒德尼姑也跑到城山庙去了。齐整的石条和青色的方砖一点点砌在了村人的院院窠窠里,就留下青青野草在缅怀过去。 和姑姑庙一同颓废的还有麻雀、树木,乃至于那窝鸻鹘。人们用鸟网网麻雀,用洋炮枪轰麻雀,用药水浸泡谷类毒麻雀。东山上有一棵老松树,估计得有几百年的沧桑,我一直梦想爬上去够着月亮,摸到太阳,一觉醒来,树不见了,丢弃不要的树梢都能当梁柁。一名退伍军人,拿着双管猎枪,瞄准悬崖峭壁上的鸻鹘扣动了扳机,将鹘鹰最后的嘶吼和舞姿从此留在记忆的天空,虽然鸻鹘最后陨落时削走他半脸皮肉。 想起了温水煮青蛙。故乡人是不是被温水煮的青蛙不敢肯定,但敢肯定的是,故乡的山水在一点点香消玉殒。再也见不到荫翳蔽日的树木了,野果树不见了,即使有几棵,花刚开出来就被虫子五马分尸,溪水不知跑哪去了,就连洗衣服都得在家洗了,潺潺的溪水和哗哗的流水成为儿时的记忆。鸟儿也许实行了计划生育,看见撒落的米粒得召开参众两院举手表决是否尝试,谆谆告诫后辈循规蹈矩是有好处的。狍子经历一次次血的教训,终于醒腔了,举家迁徙,狍子“跑之”。 孩子们这时已知道安徒生的童话了,争着做公主,可小矮人呢?可小松鼠呢?她们瞪着惴惴的眼睛看着舞台上的独角戏…… 还好,风还在唤醒,雨还在滋润,太阳还是兢兢业业,早晨爬上来,晚上落下去。月亮担心太阳落下村落太寂寞,孩子们睡觉毛愣,就领着玉兔,慢悠悠走,总不至于到天上捉走玉兔吧…… 小时候,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里,最打怵的就是冬季。原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就是为吃、穿犯愁。家乡三面环山,从早春开始,至秋风簌簌,除却自家园地出产,各种野菜、野果、野生蘑菇、飞禽走兽,总是给足你果腹的机会。二两粮时,有部分人真的放弃公职,跑到这里安家落户,只为填饱肚子。吃的问题解决了,穿的也好对付,因为一件薄薄的衣裤就糊弄过关,有时还可以不穿衣服。 冬季的麻烦就大了,野蔌一类全随着瑟瑟枯黄而销形弭迹,解决穿衣更是大问题。薄了冻得慌,厚了没那些棉花和布料,那时很少穿贴身衬衣的。怪就怪在越是冻得不行,那风婆子就刮得越起劲,那雪下得就越厚。嗷嗷尖叫的风雪直往人的脖子里灌,让人的上下牙不停地磕出声音。我的手和脚早已冻伤溃烂,咧着红红的伤口,不时地往外渗着血水。母亲就不停用打听来的偏方治,把山楂放在火盆上烤熟敷在冻伤的地方,用卤水涂抹红肿处不停地烤…… 但即使在肃杀的严寒中,孩童的天性也像早春压在石板下的小草,倔强蜿蜒地生长。故乡的冬季还是有孕育童话的深厚土壤的。只要太阳敢爬出来,只要手还能从兜里掏出来,淘气就像影子一样走哪跟哪。 河面上结了冰,孩童的嬉笑就在冰面上灵动。可以打滑刺溜,可以坐冰车,享受飞驰的快感;可以玩陀螺,比赛旋转的乐趣,自己也会转上几圈。经常磕破了手脚,浸湿了鞋袜,但浑然不觉,忘记回家后母亲的一顿烧火棍。有时也会砸开冰面,捉鱼、捉蝲蛄、捉哈什蚂,如果是很深的汀,捞出的癞蛤蟆就和哈什蚂混在一起,我们只挑红色、金黄色肚皮的哈什蚂留下,拿回家放在锅底坑里烤熟了吃。癞蛤蟆是我们唯恐避之不及的,就扔在一旁。有“五七”下放户拿回家,放在开水中一焯,将外皮蜕掉,白白的肉就喷着香气,清除内脏,上锅爆炒,让他们好一顿改善。可即使在那样饥寒交迫的年景,村人也很少食用这些东西,他们的善良淳朴让这些生灵们得以香火传承。 我还喜欢到山上踅摸。到山楂树下找寻冻透后被太阳软化再冻透再软化的山楂,既不酸得倒牙,还有汁液咂摸,味美无比。野生板栗树下还有没被花鼠和耗子捣腾走的板栗,风干,坚硬,得用牙使劲嚼,越嚼越香甜。要是运气好,还可以捞到大茧,铰开茧壳,茧蛹就在你面前一蠕一蠕,烧吃、煮吃、油炸,四个茧蛹的营养价值抵一个鸡蛋。 最有技术含量的是和飞禽走兽斗智斗勇,那是大人们的博弈场。套兔子,罩麻雀,都小儿科,小孩子们看几遍就会。打野鸡,就不容易了。连续不断地绞杀,野鸡数量明显减少,也学得乖起来,隔人大老远的。可大雪纷飞玉砌冰雕的世界里,为了觅食,也不得不冒着风险一步三抬头来到裸露地皮上。就有一个人趴在地上,一双眼睛紧盯,一支洋炮架上,“勾死鬼”(村人称扳机)一扳,上演“生死大逃亡”。 最惊心动魄热血沸腾的是众人围猎狍子。狍子很像小牛犊,若是混在牛群里或者趴在地上,真的很难分辨出来。区别最大的地方在于狍子的腿没有赘肉,且后腿比前腿长,便于爬坡奔跑,等把洋炮枪瞄准了,狍子早没影了。即使轰地一枪打断一条腿,袍子借助三条腿也会逃之夭夭。想成功围猎狍子,得诸多条件具备。瞅准狍子出没路径,在山梁顶上纠合一帮人,在大雪没膝遍地银装的山峦中,齐声叫喊,铝盆敲得叮当响,从山顶往下压,让狍子慌不择路,往山下逃窜,前腿低后腿高,一下子栽倒在雪窟窿里,双腿不着地,使不上劲。洋炮枪这时瞄上,一轰一个准。众人再一哄而上,狍子就成囊中之物。 又是雪花像个小精灵飘进孩童双眸的季节,白雪公主的诱惑再一次弹拨孩子的心灵,也弹拨着大人们的心灵。故乡传递出的信息,让我倍感欣慰,渴望变成孩童,走进童话世界。 羊肠小径终于铺成柏油路,路和河水掐架的地方,钢筋混凝土桥凌波横卧,蓄电池路灯像一个白胡子老爷爷,笑眯眯地把归家人送了一程又一程。路是政府修的,路灯是游子赞助的。在年轻人像小鸟一样往外飞的时候,一些功成名就的游子像树叶一样又飘了回来。拥有着城市的建筑、暖和,享受着乡野的空气、温馨,漂泊的心灵终于挂在故乡的枝头。再不用牛羊遍野了,再不用刀砍烧柴了,就连祖祖辈辈像命一样供着的土地、山峦,也一股脑儿流转给地界集团了,不用劳作也会获得原有土地、山峦等同的价值,这是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事呀。最让我惊喜的是,淙淙溪流中,放养了林蛙;茂密的树林中,野鸡竟可成百只窜飞;远遁的狍子经不住诱惑也寻根问祖了;让人可怕又自豪的是有人发现了狼的粪便! 西阳庵的重建已在规划中,朝钟暮鼓的梵音再次回响在幽谷溪涧中,那些兔子,那些花鼠,那些野果,那些野芍药,包括悬崖上的鹘鹰都该回来了吧。 故乡冬季的童话呢,不会远喽。飘飘摇摇的白雪精灵从凌霄殿一路滑落,将山川、河流、树木、房屋全涂鸦成银白色。这些小精灵眨着眼睛簇拥一团,招呼着红扑扑笑脸的孩童,在树枝荡秋千的花鼠,驻足凝视的狍子,低空盘旋的鹘鹰,还有笑眯眯的太阳,合不上嘴的老奶奶…… 作者简介 曹鼎毅:生于年,年从教,现工作于庄河人大。出版过《初中古诗文解析》《作文其实很简单——中考作文的四剂良方》,各类平台发表作品百余篇。 本文来自“天南地北庄河人”(ID:TNDB-zhuangheren)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anchaa.com/mysz/12163.html
- 上一篇文章: 新冠饮食,阳了以后怎么吃多吃这3类食物缓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