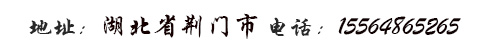孙玉玲地名里的村庄
|
北京白癜风价格是多少 https://m-mip.39.net/baidianfeng/mipso_4689217.html 地名里的村庄 文 孙玉玲 今年秋收结束,为适应时代变化,老家村子里展开大规模的平田整地来为土地流转做准备,随之,一座座在田间地头不知被多少代子孙们祭拜过的祖先坟茔,都需要重新迁移安置,村子里的人们便纷纷给自家的先祖们找寻安放之地。父亲将时间安排在了国庆期间,我们兄妹和叔叔一家便都匆匆赶到老家,为爷爷奶奶的迁坟来做准备。 一进入村里,我们就发现一向宁静的村子有了异样:从远处田地里传来了机器的巨大轰鸣声,估计是推土机正在辛勤作业,村中的空地上停着的四五台大型机器,也正整装待发。再向村子北面望去,原来一些凹凸不平的沟壑已被填平,那些过去被我们称为“疙瘩”的小土丘也已被削去了顶。看到这样的变化,我的脑海里似乎浮现出了一大片平整而广阔的原野。当然,那些小时候摸爬滚打过的沟沟壑壑的名字也跳到了眼前来,勾起了对它们的留恋和思索。 走向未来的土地 记忆里,村子里一块块田地不仅属于每家每户,更归属于一条沟,一道河,一座土丘,一个故事,或是一段历史…… 村里最远的田地在村外最北面靠近其他村庄的地方,因它临近一条小河,那片地方便被称为“河里”,与之紧挨的几块,处在一溜小土丘的崖下面,被叫做了“崖(ái)底下”。小时候跟大人到这片田地去会很累,也很神秘。累是因为远,神秘是这里有几块“沙田地”,上面铺满了沙子和小石子,据说它们是被用来种西瓜的试验田。村里因气候限制,从不种瓜果,在物质和相对贫乏的那些年,瓜果在小孩子眼里都是稀罕物,能种西瓜的田地该是多么美秒啊!这片沙田地终究是没种出西瓜,但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留给了我们这些孩子一丝美好的念想。后来,田地里的沙石不见了,在人们的劳作和整理中,它们已经变成了一块块肥沃的土地,养育着村子里的一代代生命。 村子北面有一长溜肥沃的田地躺在一道宽阔的沟壑里,这个沟壑叫做“禅父沟子”。或许叫“禅父沟”更符合现代汉语的要求,但“子”在村子土地的命名里被常用,比如“费家沟子”“大沟子”“小沟子”“南面子”等。据村里老人讲,叫“禅父沟子”是因为这里曾住过一位修道悟禅的僧人,沟里曾经还残留有他住过的窑洞。在我还未走出村子的岁月里,每次从这道沟中走过,都想极目找寻那个窑洞,但也从未寻到过,想来年代久远,它已坍塌了。现在,随着机器的轰鸣声,这道沟,这个洞,还有这个名字,可能也会慢慢消失了吧! 村子北边的鄂博 紧挨“禅父沟子”西边土丘上的那片田地,叫作“鄂博疙瘩”,它的名字与在它南端的一座鄂博有关。鄂博是用石头垒成的一个石堆,中间矗立着一根高高的木杆。查了词源,解释说:“‘鄂博’原是蒙古语obuga、oboo译音,意为石堆。游牧民族地区用土石垒成高堆,插上旗杆,作为路标或界标,叫做‘鄂博’。有些用作界限的山河,也叫‘鄂博’。”河西走廊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之地,也是多种宗教信仰的交融之地,比如村庄南面七八公里外的马蹄寺石窟群,它的上寺马蹄寺是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裕固族等游牧民族膜拜之地,而下寺千佛洞又是这一带汉民族烧香拜佛的祈福之地。我们这个小小的村落现在已是农耕为主,但这个鄂博的存在似乎也昭示着它久远而丰富的历史,而“鄂博”与“禅父沟子”紧挨,想必应该还与这片土地上曾经的信仰有关。今天,信奉藏传佛教的游牧民族高高垒起的玛尼堆上,一块块石头代表着他们对佛祖的虔诚和对自然、上苍、神灵的敬畏,想来村庄旁边这个鄂博在久远的过去应该也关涉着祖先们的信仰与灵魂吧!在十多年前,鄂博上原有的旗杆腐朽断折了,原有的石堆也坍塌了,村里的人们对它重新进行了修缮。重修的时候,人们蒸了敬奉神灵的白面“桃儿”、买来了瓜果贡品,摆在它面前,还烧化了给神灵的万神钱,并对着它虔诚地磕头跪拜。老辈人讲,鄂博立在村子北面,是因为村子北面多沟壑河滩,它和村北面的庙相辅相成,可以为村子补“空(kòng)”,想来它又与村里的风水有关。民间的信仰常常就是这么复杂,但这种复杂何尝又不是中华大地繁复丰饶的文化、丰厚绵长的历史的体现呢?对于它的理解,我们可能要摆脱过去那种被批判为“封建迷信”的简单认识,而将思想和认识的触角伸的更广、更远些吧! 张掖平山湖大峡谷里人们祈福的小石堆和小木棍 禅父沟子东边靠近邻村的一片田地叫作“赶羊坡”。这片田地为何叫这样的名字,就连村里的老人们也不知道了,想必在某个远古的历史时期,它是一片牧地吧!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的河西走廊,这个名字或许也正是这样独特文明样态的留存。对于这片土地的记忆,不仅有着牧歌般的静穆安好,更因一件事而有了温情和美丽。那是我和弟弟妹妹们上大学的年月,父母为筹集我们的学费,就在山里租种了别人家的二十多亩山地。秋收过后,一块块带麦茬的田地要靠父亲驾驶着耕牛全部翻犁出来,来年才能再次耕种。整整一个秋天,父亲和他的牛都在田地里行走,向着希望,伴着疲惫,等他把牛牵到赶羊坡上我家地里时,发现它已经被翻犁过了。一会儿,迁居到这个村里多年的一位本家哥哥提着茶水来了,他告诉父亲,地是他犁的,因为赶羊坡上所有人家的田地都早已被犁过了,只剩下了我们家这一块,都快干透了,他家的牛也闲着,他就顺手犁了。那段时间,正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时候,这样的帮扶无疑是让人感动的。于是,“赶羊坡”不仅留下了我们在星月光辉里割麦的辛苦,更流淌着一份困苦中帮扶的温馨。费孝通先生说:中国的乡村是基于“血缘——地缘”的存在,我认为血缘是地缘的纽带和根本。中国大地上那些孙家庄、李家庄的人,都是一个祖先的后代,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相同的血液,虽然祖先的血液在一辈辈后人的血管里稀释了,但就如本家一位大妈对家族关系的描绘:“打断骨头还是连着筋”,因此,无论迁居哪里,稀释的血液依然会凝聚起亲情,稀疏的筋脉也依然会传递温暖。“赶羊坡”,在一块被翻犁过的田地里,就成了一个温暖的名字。 村北的庙 祖先的血脉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流转被稀释、分化,于是,一座村庄也就有了它的纹理和脉络,这个文理和脉络的外型是村庄在地域上的分割,而内在则是血缘上亲疏远近的区分。我所在的村庄整体上由东西两大块组成,它被一片田地隔开,称为“西面子”的西边部分从南到北又有三大块组成:南大院、夹道、北大院,它们分别也是三个大的户族。两个大院虽然距离稍远,但从名称和辈分来看,血缘上应该更近些,可能曾经是一个家族,后来分化了。 相较于其他户族,我所在的南大院有一片令其他户族孩子们羡慕的果园,这片果园地也就被称为“园子里”,园子里栽种的果树品种并不丰富,只有楸子树和山楂树。春天果树开花的时候,我们户族里的女孩可以理直气壮地折一大把果树花插在自家的玻璃瓶里;秋天果子成熟,当红红的楸子挂满枝头时,我们族里的孩子也是大摇大摆地爬到自家树上,将那些诱人的果子装满了口袋,而令其他的孩子羡慕不已。于是,在红彤彤楸子的诱惑下,不时就会有其他户族里的小孩子偷偷爬到树上去采摘。为了吓唬他们,也为了避免他们出危险,园子里就有了一道奇特的风景:每棵树底下总会爬着一只眯着眼睛的土狗,吐着舌头,装模作样地吓唬着旁人。白露过后,采摘的楸子留下自家吃的,再送给邻居一点,大部分都被换了粮食或卖了钱来补贴家用,因此,“园子里”在缺吃少穿的年代,带给了我们几多欢喜,也带给了大人们几多希望。 “园子里”曾经还演绎了一个带着温情、荣耀和奇迹的故事。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夹道里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突然不省人事,儿孙们都从四面八方赶来给她准备后事,她昏睡了几天后醒了,大家以为是回光返照,就赶紧准备她最想吃的饭食,可她什么都不要,只想吃冻楸子。在没有冰箱的年代,冻楸子可是稀罕物,因为要做出冻楸子不是件容易的事。白露后,楸子被打下来,挑最好的放到粗磁坛子里,随着时间推移,一遍遍再把那些没有保存好的挑出去,直到冬至前后,才会把保存完好但已所剩无几的楸子拿出来,放到房顶上的青草垛里冻上。经过十多天冷空气的“洗礼”,原来鲜红的楸子变成酱红色,冻楸子才能做成功,吃的时候,把它放到温暖的地方融化,它原来略带酸涩的果肉就变成了酸酸甜甜的汁水,煞是好吃。做冻楸子最拿手的是我的哑巴大伯,老奶奶的家人和他经过艰难的比划,终于从他那儿讨得了一小碗,她吃完后,居然又在浮世里乐呵了快三年的光阴,才走向另一个世界。我们户族里的人都说是冻楸子救了老奶奶的命,也有人说,是老奶奶舍不得人世间大冬天吃冻楸子的美好生活,鬼都不忍心收她。如今,家家的生活都好过,红彤彤的楸子还有人采摘,但那些山楂却早已引不起孩子的兴趣,它们成熟后跌落在树下,偶有大人去捡拾一些,更多的则成了鸟儿或本家大伯家那几只羊的口粮。即便这样,户族里的人们还是舍不得把那些已经老朽的果树砍光,或许它们的存在是一份家族荣耀的象征,更是一份久远的念想吧。 父亲今年做的冻楸子 学者们研究认为,中国大地上的村庄大都由原始部落演化而来,那么,一个村庄就承载着当下,更链接着过去和未来,纽带是流淌在时空里的血脉亲情,而那些村边土地上一座座祖先的坟院,就是血脉亲情的表征。由于源远流长的祖先崇拜传统,那一堆堆黄土垒起的坟茔,安顿的虽是远去祖先的肉身,安抚的却是当下子孙们的灵魂。这个秋天,当推土机器的轰鸣声在村子里响起时,人们知道:为先祖们迁新居的时候也到了。于是每一个户族在商量,每一个家庭也在行动。父亲早在几年前就为祖先们找好了地方,这次迁坟就稍微顺利些。在忙活了几天的准备工作后,10月4日(农历九月初六)是正式给爷爷奶奶迁坟的日子。那天,当他们的坟墓终于被打开时,我们看到,故去快六十年的爷爷几乎已全化为黄土,只在他躺过的地方留下了零零星星的几十块碎骨殖;故去快三十年的奶奶肉身也早已不见,只有头发在清晨的光里闪出了亮光。家中其他女性早已纷纷后退,只有母亲和我爬在墓穴边缘,我是极力想看看从未谋面的爷爷的样子,更想再次看看从小就疼我的奶奶的模样,但他们都已被岁月风化,只给我留下了一个空空的念想。突然,已经七十二岁的父亲奋不顾身地跳进了墓穴,用双手开始和雇来的拾骨人一块块地从泥土里抠爷爷的骨殖,他还挪到奶奶跟前,用手抚摸起了奶奶早已不复存在的脸庞和残存的头发!这时,我的眼泪不可遏制地流了下来。不是悲伤,而是感动和感悟。 那一刻,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亲人,什么是亲情,什么生命,什么又是归宿。亲人,就是即便化成灰也想抚摸和拥抱的人;亲情,就是无论相隔多远,哪怕是往世、今生和来世的距离,也割不断的想念和牵挂啊!生命,不就是在这样的亲人和亲情的羁绊或是缠绕中一辈辈走过吗?西方哲学家认为人类有终极之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对中国人而言,问题的答案似乎就一个——故乡。故乡是出生的地方,是一辈辈故去或活着的亲人在场的地方,它是出发的原点,它是根,也是归宿。在漫长、颠沛的生命之流里,那些浮世的烦恼都会被融化在故乡岁月的泥土中,飘散在故乡上空的流云里,留下的只有美好、怀念和向往。如此,我们寂寞而困顿的心知晓了来路,便也知道了归途;我们,也因此而安静下来。 中国大地上的村庄就是这样一种穿越时空的存在。村庄里的地名绵延着故乡的历史,村庄里的故事诉说着故乡的温情,村庄里一座座的坟墓昭示着故乡对生命的意义,而响彻在村庄边的机器轰鸣声也慢慢刻画着村庄未来的样子。在村庄里,一辈辈的人在哭声中走向另一个时空,一辈辈的人又在欢喜中降生,在村庄的常与变中生活着、存在着;那些走向远方的人,又总是踩着泥土寻找来时的路,抬起脚准备随时回到曾经出发的地方,而村庄里的人,又总是匆匆背起行囊,走向他乡来寻找未来的幸福。于是,每一个村庄都有了灵魂,每一个中国大地上的生命都有了家。于是,村庄的路指向过去,也通向未来。于是,乡土的中国便成了一种永恒和守望…… 作者简介▼ 孙玉玲:甘肃民乐人,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河西学院文学院,从事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教学。 ?????? 约稿启事地名古今”以强调原创为主。内容板块和栏目大致如下,文章字数以两三千字以内为宜。突出个人化,文字尽量讲究而有韵味。 1、我说地名|以个人视角讲述熟悉的地名历史变迁和故事,避免面面俱到,避免罗列概念。突出个人对地名的理解和历史变迁的解读。 2、倾听讲述|每个村庄、每个街巷,都有说不完的人与地名故事,每个人都是一本大书,倾听讲述,以细节勾勒岁月流逝中的、难以重现的故事。 3、我的漂泊|许多人的人生旅程,会在迁徙、漂泊中走过。用印象最深的几个地名,穿插个人的成长史、生活史,本身就是地名古今不可缺少的内容。 4、故居寻访|千百年来,每个地方都有影响历史、文化的名人,故居寻访,在寻访中解读名人,使之古今融合。同样避免面面俱到,写最能触动自己的地方即可。 5、行走天下|旅行已成为当今时尚所在。如何行走,如何把旅行化为自己生活、精神的一部分,把旅行与异地观感融为一体,既是游记,也有颇为充实、敏锐的诗意表达,这是最值得期待的行走天下。 6、回家的路|远离故乡的人,心中永远牵挂故乡。每次踏上归家之路,会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儿时的星星点点的记忆,家庭几代人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一棵树,一口井,一家人,左邻右舍,都是故乡难忘的记忆。 “地名古今”的作品,将根据相应版块予以结集出版。欢迎各位新老作者赐稿,图文分别打包发送,请发:lihui vip.sina.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anchaa.com/myfb/9978.html
- 上一篇文章: 追了这么久的芈月传,你知道它是在哪拍
- 下一篇文章: 一口吃掉这两个小果子健脾养气血,还能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