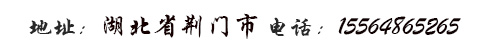李安超随笔一颗小山楂,一段父子情
|
李安超随笔—— 一颗小山楂,一段父子情 (二)在我爸四十岁我二哥十岁那年,我妈在屋前的簟基里给他们俩拜过佛,缙云农村有一个规矩是“贺三不贺四”,四十岁的生日要低调在,之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是因为拜佛用的水果、糕饼、糖果被我一人吃了不少,我的两个哥哥在小学,没人跟我抢,毕竟在农村,有好东西吃的机会并不多。 我爸那一年却是走背运,还是春天的时候,他跟村里的景禄叔用铅丝扎成手镯形状,拿到电镀厂镀成锃亮的银色,装在蛇皮袋里拿到江西去卖,却是一个也卖不出去,空手而归,车费还有材料钱倒贴了进去,回来后这些手镯送人都没人要,这是第一个不顺。从江西回来后,又跟着乡人去安徽黟县帮人烧炭,在深山老林里砍柴烧炭,个中辛苦自不必说,可恼的是烧好的炭却卖不了钱,于是负气而归,挑着棉被走到一处工地,将棉被低价售给工人,一路轻装走到贛皖交界,在夜晚听到火车轰鸣声,大喜过望,坐火车回金华,再坐车回壶镇,从壶镇走到双溪口,村民告知他的堂哥遭遇横祸,死于非命,谋生不易,亲人故去,父亲心情之低落自然是可想而知。将堂哥安葬后,堂嫂家盖房子,盖房用的条石、水泥板都是要人力抬上去的,我爸自然是当仁不让地去帮忙,在抬水泥板上三楼的时候,硕大的水泥板从绳里滑下来,砸中了父亲的胸口,父亲昏死过去,亲戚们连忙医院,并告知了我母亲。我母亲听到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医院,医院的大夫见我妈一个农村妇女,语带讥诮地问我妈带够钱没有,我妈很生气地拉开装钱的包,冲他喊:你看够不够!所幸我爸只是肋骨折断,出院后在家里躺了一段时间就好了,不过因为堂哥刚死,堂嫂也很困难,医药费自然也只能是自己掏出。 条石墙是用人力二人爬木梯一层层抬上去的 但命运对我爸的磨难并未结束,伤好后,还是秋天,我爸想着还是应该出去赚点钱,他就跟着北山的一个窑厂老板去永康上下丁那里做瓦,可惜他跟的是一个欠债老板,老板起家的钱都是借来的,干到年底一分工钱都没拿到,只是写了张元的欠条给我爸,于是从89年到我毕业的03年,我爸每年过年前都要去北山讨债,那一家人却是每况愈下,日子过得一年不如一年,父亲每次都是空手而归。我爸年轻的时候也跑过好多地方,吃过不少苦头,但儿时的我却从没看到他消沉过,他总是很乐观。 防火道的右边属仙居 (三)年复一年,当花从枝头凋落,绿叶也就成了主角,麦子开始抽穗,洋芋的枝叶也变得茁壮,那高低起伏的山丘上,安葬着我们的先祖,那里也将是我们最终的归宿。口中食、身上衣、居之宅、浴之溪,在这方热土里获取,最终在这里安息,曾经有个九十岁的老人,在逝世前的那一年,独自一趟趟地从村头走到村尾,又从村尾走回村头,他心里可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留恋,或是想记住这片土地的模样,还是一路寻找那从前的点滴时光?云雾低沉,四野苍茫,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高山不改其巍,溪水不变其形。 海临尖 (四)一颗小山楂,一段父子情。在我还没上小学前,我爸的收入来源主要就是砍柴。跟现在漫山遍野都是树木不同的是,八十年代的山上树并不多,而且是村集体所有,要砍柴只能翻过高耸的赫临尖,到仙居那边去砍。当东方微明,我们还在睡梦中的时候,父亲推着独轮车,腰间绑着柴刀,带上母亲头天做好的大麦馃出发了,从宫前出发,走8里路到管溪村,管溪进去再走6里到洪坑岭水库,将独轮车放下山脚,开始爬山。父亲走的这条路,其实就是侍郎公李棠“游独山记‘’走的路线,李棠出发时是肩舆而行,携儿带仆,父亲却是孤身一人,李棠眼中所见是云雾廓清,旭日澄霁,父亲想的却是要早点到达目的地。山路崎岖、磴道萦纡,山脚到独山殿约6里,独山殿到括苍林场约3里,再爬5里山路到赫临尖,翻过山顶,一路下去约8里到达仙居,此时已是中午。吃过麦馃(无馅,只有盐油涂抹)砍好柴,用梗藤系捆,柴杠戳入柴堆,挑上肩膀,返程。挑柴上山的路是最辛苦的,我也曾从南田走到长坑脚拜佛,回来的五里山路就让我叫苦连连,而父亲却是要挑一百多斤柴,而且走的路更差,更长。 汗水淋漓地爬过山顶,下山的路就略显轻松了,原路返回走到山脚,将柴放在独轮车上,一天的劳作才算完成大半,后面用独轮车推回来的十几里路对他而言已经不算负担。父亲推柴回家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要下山,儿时的我常会飞奔向前,问他讨要山楂,父亲带回来的山楂总是色泽紫红,肉厚味甘,多的时候有七八个,少的时候三四个,后来我年岁渐长,在宫前的山上也摘过山楂,却总是又小又硬又酸,再也没有从前的味道,我想高山上的山楂才是最好的。脚不停蹄的爬山,汗流浃背的挑柴,在灌木林里,在荆棘从中,看到那红色漂亮的山楂,父亲的心里该是多么的欣喜,有了好吃的山楂,就可以带回去哄哄馋嘴的孩子,挑柴是很辛苦,却可以养家,山楂并不起眼,却有着为人父的慈爱,我想正是因为心里装着那份对家人的爱,才支撑着他走完那漫长险峻的山路。 扫描或长按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anchaa.com/mygx/8164.html
- 上一篇文章: 山东苗木求购信息4月30日
- 下一篇文章: 青年记者践行ldquo四力rdqu